一部让大地战栗的轮回史诗:莫言《生死疲劳》中的苦难与救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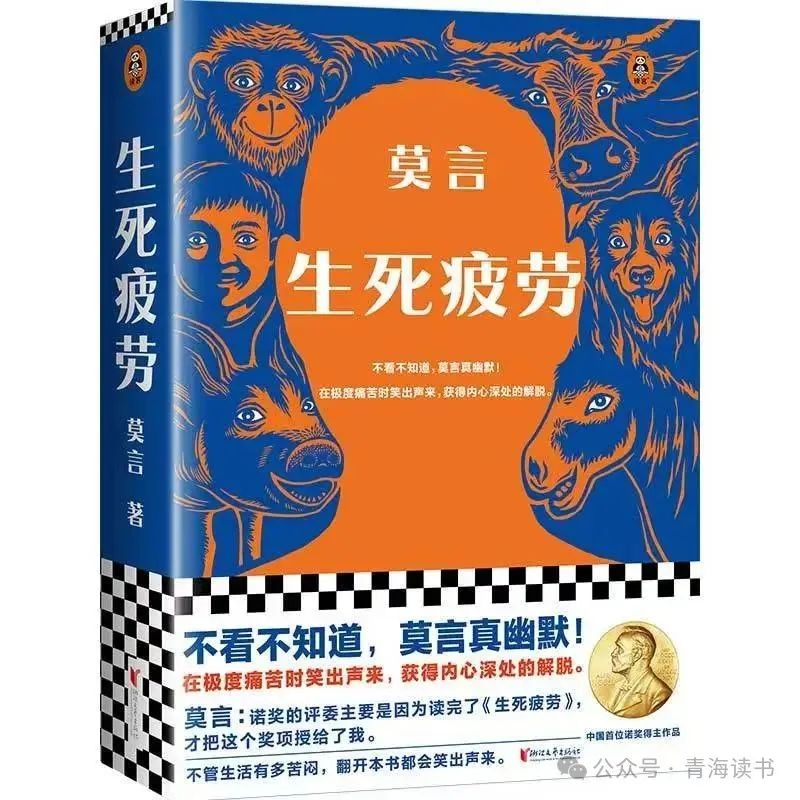
1950年的一声枪响,让高密东北乡的地主西门闹含冤而死。他做梦也没想到,这声枪响并非生命的终结,而是一道穿越生死的神秘之门——门后不仅是六道轮回的奇幻历程,更承载着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。
从转世为驴的倔强、托生为牛的犟劲,到化作猪的贪婪、成为狗的忠诚,乃至变作猴的机敏,这些动物形态下的生命体验,最终都凝结在大头婴儿蓝千岁清澈的目光中。透过动物的瞳孔,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土地深处的血脉搏动,见证时代浪潮里的沧桑巨变。
作为80后,我对五六十年代的往事本感陌生。但在《生死疲劳》中,西门闹转世动物的视角,让“打土豪分田地”“大炼钢铁”“人民公社”“包产到户”等曾显疏离的政治术语与历史事件,有了清晰的轮廓。那些时代印记,在“驴折腾”“牛犟劲”“猪撒欢”“狗精神”的生动演绎中一一铺陈。故事虽荒诞离奇,主题却严肃深刻,让人于笑中带泪的阅读里感悟,在感悟中实现自我精神的升华。
莫言曾透露:“诺贝尔奖评委主要是因为读完了《生死疲劳》,才将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了我。”这部作品从酝酿、构思到完稿,跨越43年光阴,他以43天的酣畅疾书,用45万字的宏大篇幅,将民间想象与历史苦难巧妙熔铸,成就了这部“遗憾最少的巨著”。余华曾这样精妙点评:“假如要用中国文学里某一本书的书名来解释《活着》写的什么,用《生死疲劳》是最好的。反过来也一样,如果你要解释《生死疲劳》讲的是什么,那就是《活着》。”这番话道破天机:中国农民半个世纪的坚韧顽强,早已镌刻在六道轮回的宿命年轮中。
轮回,是映照历史荒诞的魔镜。西门闹的六道轮回,恰似一部在时代刀刃上行走的中国当代史:驴的嘶鸣声中,裹挟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激昂号角,最终沦为饥民果腹的分食之物,这荒诞结局正是集体狂热最尖锐的隐喻;化作耕牛的西门闹,以倔强之姿抵抗人民公社的浪潮,却在儿子西门金龙将烧红烙铁刺向自己时,见证了血缘、亲情、伦理在政治暴力面前的脆弱不堪;转世为猪的岁月,恰逢文革的混乱狂潮,西门猪称霸猪圈的荒诞场景,恰似权力更迭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缩影;变身为狗后,它以冷眼旁观改革开放的浪潮,蹲踞在副县长南解放一家生活周围的姿态,洞穿了人性在物质洪流中的异化与迷失。莫言以动物视角,巧妙解构了宏大叙事的神圣外衣。当西门驴目睹二姨太改嫁长工蓝脸,听见亲生儿女金龙与宝凤唤烂脸为“爹”时,那颗困在牲畜躯壳里的人心,无情戳破了历史教科书粉饰的表象,将个体命运的血泪伤疤,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眼前。
执念,是贯穿《生死疲劳》的永恒锁链。莫言以“生死疲劳,从贪欲起。少欲无为,身心自在”的佛偈题记为刃,精准剖开人性的内核:西门闹的冤魂因放不下前世冤屈,坠入畜生道的轮回深渊,在驴、牛、猪、狗的皮囊下反复咀嚼背叛、疏离之痛;蓝脸的“执”则是另一种极致——当集体化浪潮席卷大地,他振臂高呼“天下乌鸦都是黑的,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”,用单干的倔强与整个时代对抗,最终陷入众叛亲离的孤独绝境;与其相对应的是其儿子蓝解放在深陷婚外情的泥沼后,以野火燎原之势焚毁仕途、抛妻弃子,当他不顾一切追逐所谓真爱并最终被世俗认可之时,却在挚爱之人庞春苗车祸的轰鸣中结束了了这闹剧般的所有,让人唏嘘,原来,一切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审判。
贪欲是执念的具象化呈现,它如同盘根错节的毒蔓,将众生困缚其中。《生死疲劳》里,洪泰岳从热血革命者堕落为权力的奴隶,西门金龙为追逐“进步”罔顾继父蓝脸的养育深恩。这些被时代浪潮席卷的灵魂,恰似命运棋盘上无力自主的棋子,印证着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洞察:“生死疲劳,本质是人生、死、疲、劳四种生命现象的循环,皆源于贪念,终以苦痛收场。”
现实中,追名者机关算尽,逐利者众叛亲离,求权者丧失本心。无论手段如何隐蔽,都逃不过良知与时间的审判。小说中每一次荒诞的轮回、每一个执着的灵魂,都在拷问人性欲望的边界,于虚实交织的叙事中,映照出时代与个体共同背负的精神枷锁。
在血泪浸润的土地上,绽放超越苦难的生命之舞。莫言以黑色幽默为笔,将时代的深重苦难熬煮成荒诞的诗词:西门猪溺亡时,以英雄之姿拯救落水儿童;西门狗在黄合作家庭濒临破碎之际,始终不离不弃,更对其子南开放悉心照料。猴戏班子的锣鼓声中,世纪末的黄昏徐徐落幕,死亡与新生在戏谑狂欢里达成和解——荒诞表象之下,涌动着对生命最深刻的礼赞。
书中的女性形像,堪称苦难长河中真正的摆渡人。正如莫言在采访中所言:“每到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,女人要比男人坚强,女人要比男人伟大。”这一深刻认知在《生死疲劳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:西门白氏在西门闹被枪毙后,以隐忍之姿坚守善良本性;西门宝凤守寡后独自撑起破碎的家庭,在风雨飘摇中挺直脊梁;黄互助屡遭丈夫西门金龙的背叛,却仍以仁爱之心向街坊邻里伸出援手,用善意消解命运的恶意;黄合作遭丈夫抛弃后,依然在食堂默默劳作,以“哭着是活,笑着也是活”的豁达,诠释生命最本真的韧性。即便作为蓝解放与黄合作婚姻中的第三者,庞春苗身上那份纯真质朴的唯爱特质,也让人难以心生恨意。这些女性以沉默的坚守,编织出超越苦难的精神经纬,成为支撑那个苦难时代的温柔力量。
当携带血友病的大头婴儿蓝千岁降临人世,平静回溯六世轮回的记忆时,五十年的仇恨与恩怨,在新世纪的晨光中悄然消融。莫言将佛教轮回观与中国农民的生命力激烈碰撞,迸发出穿透苦难的精神星火:“世事犹如书籍,一页页被翻过去。人要向前看,少翻历史旧账。” 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豁达注解,更是对时代沧桑的深情和解。
2000年元旦的钟声里,蓝千岁睁开承载着六世记忆的双眼。这个血友病患儿,终于挣脱仇恨的锁链,以一句“我的故事,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”,将西门闹地狱归来的怨气化作释然的微笑。这抹微笑,是历经轮回沧桑后,对尘世最温柔的终极谅解,更是对生命超越性力量的永恒礼赞。
《生死疲劳》恰似一面魔幻照妖镜,将权力的虚妄、欲望的狰狞、历史的诡谲尽数映照;又仿若一剂苦口良药,以荒诞解构苦难的沉重,用笑声消解死亡的阴霾。这部浸透血泪的“农民史诗”里,莫言以笔尖为刃,剖开时代的肌理,让读者在啼笑皆非间窥见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韧性。
合上书卷,莫言那句“最好的生活,就是在痛苦的时候,笑着面对”愈发掷地有声。这笑声绝非对命运的妥协,而是历经六道轮回的淬炼、尝遍生死疲劳的况味后,对人间万物最深刻的慈悲。它是看透世事荒诞后的从容,是在苦难中生长出的生命智慧,指引我们在无常的岁月里,依然保有向光而行的勇气。
罗曼·罗兰曾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”当我们见证了西门闹的六道轮回后,是否也能如这般坦然地拥抱生活,成为自己的英雄?
后记:当我仍沉浸在《生死疲劳》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妙的文学技法中时,儿子小宝已经迫不及待地从我手中接过了这本期待已久的书。看着孩子热切翻开书页的模样,我不禁思考:这部作品是否适合他这个年纪阅读?但转念一想,与其强行阻止他的阅读热情,不如以这篇小文稍作引导。希望他能透过那些略显直白的文字表象,真正领悟到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精髓。
白雪,甘肃天水人,现定居青海大通,热爱文字,喜欢阅读,青海读书会签约作者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