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在线寻秋·秋风战队】秋雨染大通,一叶一念忆祖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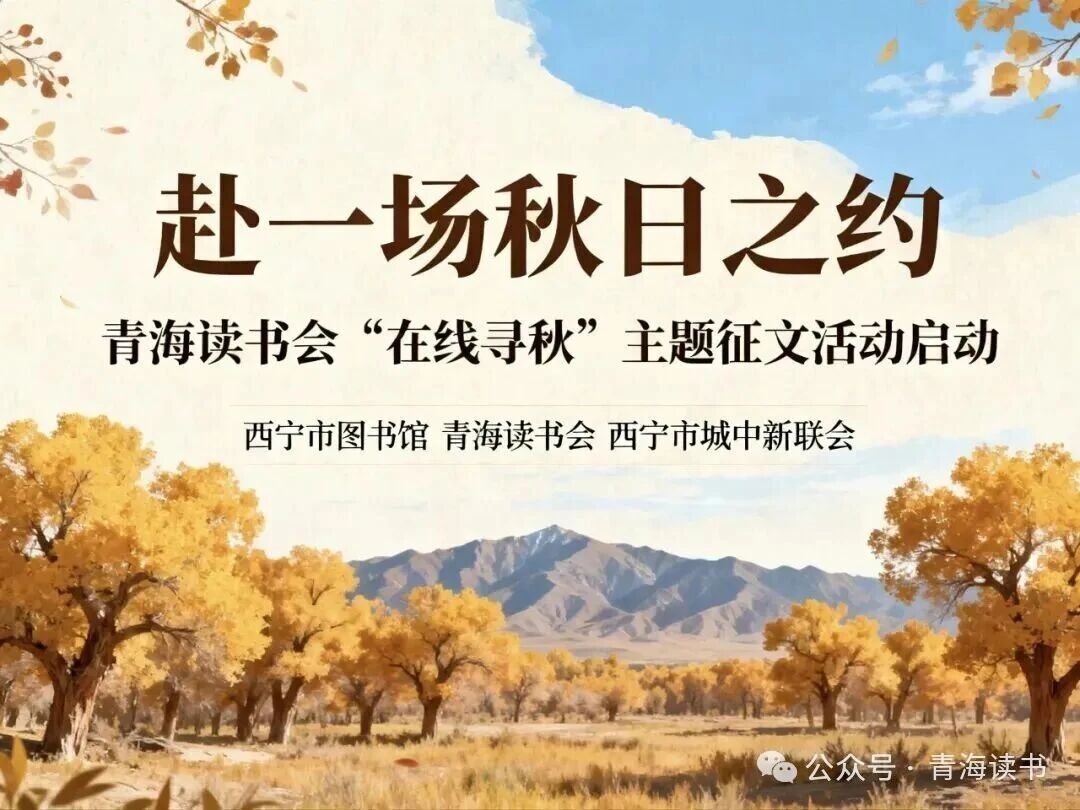
赵海燕制作
大通的秋天来得让人有些猝不及防。国庆前夕,仍是艳阳高照,暑气未散,大有延续夏日之势。在一天天盼望为祖国庆生的焦躁等待中,心中不免沾沾自喜:嗬,今年怕是可以穿着短袖过这国庆、中秋双节了!路旁的树木依旧一身绿装,更让人欣然感慨:今年的秋天,比去年来得晚多啦。尽管早已记不清去年秋意是何时降临的,但人就是这样,总习惯把希望寄予明天,总愿意相信一年好过一年。至于天气,当然是春暖夏凉、秋温冬热最好,谁又真去计较季节错乱的后果呢?普通人嘛,幸福感常常就建立在最直接的体感之上。
谁料,骤然而至的降温仿佛成心捉弄那些计划秋游的人们。国庆一到,秋雨洋洋洒洒,转眼染红了枫叶;秋风飒飒一吹,柳叶杨叶也跟着泛了黄。熟人见面,第一句话往往是:“穿秋裤了吗?”接着便彼此展示起御寒的成果。说好的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呢?那胜却人间无数的美景与美好感受,似乎并未如期降临——但,真的没有吗?
别急。不妨在瑟瑟秋雨暂歇的间隙,穿好冲锋衣,出门走走吧。漫步林荫小道,清新的泥土气息沁人心脾。雨水压住了浮尘,眼前一片明净。瞧,地里的青头萝卜悄悄探出了头,圆滚滚、翠生生的,像胖娃娃的手臂;这边的农民伯伯也趁着雨歇抢收土豆,湿润的土地上,躺满了白生生的“小皮球”。这些熟悉的农作物,让人心生亲切却不觉惊奇。最叫人喜悦的,反倒是那些原本叫不出名字的植物,因结出果实,终于“验明正身”:哦,原来那片不是芹菜,是胡萝卜呀,你看都蹿这么高了;哦,那是大豆,不是我们误认的棉花株……任何一种庄稼初现真容时,都让人忍不住联想到“新鲜”“甘美”“丰收”这样的词。
而当你正沉醉于秋天这丰饶的土地时,不妨再想象一下:一片片金黄、半黄,甚至五彩斑斓、如花蝴蝶般的落叶,轻轻落在你的发梢、肩头、脚边……那一刻的陶醉,是不是所有诗词与语言都难以尽述?不必回答我,静静感受就好。因为那一刻,我确实触摸到了秋天的幸福——那幸福,有温暖亲情的包裹,也有爱而不得的缺憾所带来的凄美,更有内心沉淀之后的清醒与踏实。
那一刻,我对未来的想象斑斓多彩如秋叶,内心的信念坚实厚重如大地,而所有祈愿,都像秋夜的明月一般清朗明亮。
人是情感的动物。于我而言,虽不至于见花开花落、秋风秋雨便感时溅泪,但确实是个富于联想的人。就像这秋夜的明月,总能轻易牵起我记忆里的丝线,让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中秋往事,顺着月光慢慢浮现。
少年时,逢中秋月圆,最爱吟东坡那句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。那时年纪尚轻,其实并未真正读懂词中深意,只觉得这“问青天”三字,与屈原的《天问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,都透着一股探索天地的傲气劲儿。后来虽明白二者风马牛不相及,却依然沉醉于那份字里行间的豪迈与乐观,为之倾倒不已。
只是那时的“豪迈”里,还带着未经世事的轻盈——直到岁月将我推入略带尴尬的中年,直到某个同样弥漫着果香的中秋,祖母的身影在月光下渐渐清晰,我才恍然读懂,那诗句中藏着的,是一种远比“探索”更为深沉的牵挂。
再后来,长大了,离开了家乡。又到中秋月圆时,心中浮现的已是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辽远,是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的怅然,是“月是故乡明”的眷念。是啊,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而今步入中年,才真正懂得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”里的无奈与喟叹,也有了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沧桑体悟。
于是渐渐明白,所谓生活,或许正是“人生哪能多如意,万事只求半称心”这般——不必圆满,但求心安。
而这份“心安”的分量,是祖母用她最后的时光,在我心里刻下的答案。那年秋天,工作与人际交往双双受挫的我,回到家陪伴已八十七岁高龄的祖母。中秋那天,多日进食甚少的祖母,望着桌上的月饼,用极细微的声音对我说:“给我吃点月饼。”我欣喜不已,赶忙取来月饼,小心喂她,又匆匆唤来母亲。我们看着她慢慢吃下小半块月饼,心中涌起一股激动的期盼——祖母一定不会有事,哪怕年老体弱,也还能陪我们走好几年。
祖母吃完那小半块,便轻轻摇头,不再吃了。我仍劝她再多吃一些,说多吃才有力气。她却只是摆摆手,接过母亲怀里的小侄儿,用那张布满皱纹、瘦得只剩一层皮的脸,轻轻贴了贴孩子柔嫩的面颊,低声说:“我要给我的小重孙腾地方了。”我们明白她的意思——嫂子即将生产二胎,母亲为了照顾祖母,一直与她同住一屋。祖母是觉得,自己走了,母亲就能专心照顾小侄儿,为嫂子分忧了。
我和母亲眼中含泪,一时语塞。还不懂事的小侄儿,却在太奶奶的怀里咯咯笑起来。
“我走了,若是真的在天有灵,我会保佑你工作顺利,感情称心如意的。”祖母望着我,轻声续道,“好孩子,你要每天都开心一点。”
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:“我不要您走,奶奶,什么都不如您在我身边重要。”
“傻孩子,人有生就有死,哪能不走呢?”祖母一脸平静。
中秋假期结束,我返回学校。没过两天,祖母的身体就急转直下。父母和姑姑们为她换上了预备好的寿衣。因我体质弱,他们不让我再进那间屋子。我心急如焚,只能透过玻璃窗偷偷望去——瘦小的祖母被裹在宽大、色彩浓艳的传统寿衣中,我甚至看不见她的脸。
一向不算迷信的我,竟也开始默默祈求上苍:“我愿用我十年、二十年的寿命,换奶奶健康起来。”
可上天没有回应我。八月二十的清晨,祖母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从她离世到出殡,秋雨一直绵绵不绝。我心里难过得像被掏空,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来。我甚至有些恨自己——连老天都在为奶奶落泪,我却哭不出来!
祖母下葬后,我们从坟地回到家。我终于再次走进那间屋子,看见她曾经躺卧的地方空空荡荡,泪水仿佛瞬间冲开了闸门,再也抑制不住。一旁的婶子们低声埋怨我:“该哭的时候不哭,这会儿好不容易把你两个姑姑劝住了,你又惹她们伤心。”
我知道她们说得在理,可眼泪就是止不住。
祖母彻底离开我们那夜,雨下了一整晚。我听着窗外的雨声,想到她一个人躺在毫无遮蔽的墓地里,心如刀绞。从那以后,每年秋天夜雨敲窗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辗转难眠的雨夜,想起祖母。
祖母一生睿智豁达,在生活的重压下,她以坚韧的意志独自将父亲、叔伯和姑姑抚养成人。她对我们这些孙辈尤其慈爱,那份温暖贯穿了我们成长的每一步。步入人生的秋天,祖母既享受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,也尝尽了比生活本身更苦涩的滋味——儿子们因赡养问题产生的纠葛,为她的晚年添上了一笔萧瑟。最终,在那个西风渐起的秋日,她与世长辞,带走了一生的艰辛与奉献——那是一段深爱与隐忍交织的厚重人生。
我不敢也不忍细细回望祖母一生走过的路,只愿在每个秋日里,静静记住她柔韧一生的坚持,和她给予我们那份时光带不走的满心慈念。
在这个同样属于农历八月二十的日子,我提笔写下关于祖母的回忆。并非为了煽情,只因我深知,无论过往的文字里如何描摹秋天的静美,如何赞颂它带给人的沉淀与沉稳,骨子里,我依然与千百年前的古人同感——那份“常恐秋节至”的彷徨,始终是我性格里逃不开的敏感底色。
但“恐”归“恐”,秋终究会来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于是,我学着在这座被称为“冷美人”的大通小城里,认真走过她的秋天。
我会与儿子小宝一同漫步,在街边寻找一片完整而颜色鲜亮的落叶;在秋雨迷蒙时,遥望云雾缭绕、恍若仙境的老爷山;踩着层层叠叠的落叶,为意外发现的一朵蘑菇而惊喜;看大通河上圈圈漾开的涟漪,几只野鸭悠然地拨开清波;或在大通公园那水平如镜的人工湖上轻轻泛舟。
我也会尝一颗酸甜的鲜红海棠,低吟一句“酸甜藏就岁寒心,风露揉成蜜色深。”
于是,秋天不再只是萧瑟与“悲寂寥”的代名词,秋风秋雨也褪去了“愁煞人”的凄凉。放眼望去,秋日的光景,竟也变得如此明快、鲜活而可爱。
白雪,甘肃天水人,现定居青海大通,热爱文字,喜欢阅读,青海读书会签约作者。

